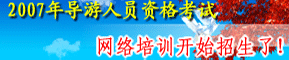妇好(xiāo)尊——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
“妇好尊,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郑振香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说,“妇好尊安置在妇好墓墓底,墓底距墓口7.5米,已经深入水下1.3米。尽管当时我们调过水泵抽水,但岂料水越抽越多,根本抽不干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国宝的安全,我们就只好下去摸国宝、捞宝藏。”
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吊上来的时候,妇好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主持妇好墓发掘的郑振香研究员回忆说,“其他的器物,如司母辛鼎等,以前大家都见过与之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我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30多年过去了,对此,我记忆犹新。
“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于是,这两件器物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尊’。之后,在研究器物时发现口下内壁上有‘妇好’铭文,于是我们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尊’。”
这时的“妇好尊”,缺少半个“脑瓜”——这两只“猫头鹰”,还没“生”出后脑勺!
考古学家以为,妇好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可流入液体,就是酒呀!”郑振香说。
但考古学家对合青铜残件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对合者都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
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朴实的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
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尊,予以验证。
“恰好那两个器物,能分别与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个完整的脑瓜。此时的‘猫头鹰’,头呈弧形,再衬以盖上的装饰立鸟(躲在大猫头鹰耳朵后面的一只小猫头鹰)、夔龙(尊盖的龙形把钮),尊这才完美无缺。此时,再看妇好尊,双眼圆瞪,双腿粗壮,双耳耸竖,喙宽尾敛,挺胸昂首,傲视天下,雄健刚毅,堪为‘战神’。”
猫头鹰视野开阔,甚至可以把头扭过180度,越过肩膀观察环境;它翅膀宽大,羽毛的边上有天鹅绒般密生羽绒,能使其飞行无声;它昼伏夜出,以鼠类为主食,为农林益鸟。猫头鹰夜视能力更强,耳的上方羽簇直立,其功能是集中声音。猫头鹰两侧耳孔开口位置不对称,两耳对频率不同的声音敏感程度不同,因此可同时在两个平面上定位声源。科学家曾就猫头鹰捉杀老鼠的过程,做过一项科学实验:把猫头鹰关在一个全黑的房间里,用红外摄影设备观察它的杀鼠行动。实验做得非常巧妙。室内除地面上撒下一些碎纸条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实验开始,鸟类学家把一只老鼠放入实验室,开始录像。从录像上发现,只要老鼠一踏响地面的碎纸,猫头鹰就能快速、准确地抓获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环境中,猫头鹰的听觉,起的是定位作用;它的无声出击,让猫头鹰的进攻更具“闪电战”效果。
武丁“双后”青铜“双曜”
说到妇好尊,不能不说司母戊大方鼎。
在妇好墓中,与妇好尊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由此,科学家断定:“司母辛”是妇好的庙号。
与“司母辛”一样,“司母戊”也是庙号。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司母戊”是谁呢?
解读甲骨文祭祀谱,科学家们发现,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分别是:妣戊、妣辛、妣癸。“由于‘司母辛’铭铜器与‘妇好’铭铜器大量共存于一墓之中,我们推测,两者当是一人。这就是说,‘妇好’是墓主之名,‘辛’是她的庙号,‘妣辛’是武丁子辈对其法定配偶‘辛’的称谓。这一发现,为解决卜辞中‘妇好’与‘妣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郑振香说。
顺着这一思路,科学家对司母戊大方鼎与司母辛大方鼎的成分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合金配比惊人相似,可能是同一时代生产的器物。而从形制上看,考古学家早已断定,两者是同一时期的器物。
由此,再结合武丁有三位法定配偶,即妣戊、妣辛、妣癸,可以推断:“戊”,就是“妣戊”,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为祭祀武丁的这位庙号是‘戊’的法定配偶,由武丁子辈铸造的。
- · 寻访濮阳“中国杂技之乡”[2008-9-28]
- · 充满历史底蕴的河南地名[2008-9-28]
- · 伏牛山的奇特来历[2008-9-27]
- · 北宋为何定都在开封?[2008-9-25]
- · 扑朔迷离的开封古转兵洞[2008-9-23]
- · 宋廷“狸猫换太子”,何来狸猫?[2008-9-22]
- · 大小便称为“解手”,根源何在?[2008-9-18]
- · 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是否存在?[2008-9-16]
- · 颛顼和帝喾,传说时代的华夏英雄[2008-9-12]
- · 要问祖先在何处,大槐树下老鹳窝[2008-9-11]

- 酒店
- 特产
- 娱乐
- 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