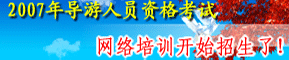探访塔克拉玛干“野人部落”
克里雅,维吾尔语“飘移不定”的意思。地图上的克里雅河像把尖刀,深深插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沿河南北纵横足足200多公里,都属于同一个村——它就是达里雅博依村。
这么大的村,却只住了200多户人家——他们就是克里雅人。
几百年来,一直如是,从不改变。
一个不知来自哪里的族群
1896年1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最早发现了克里雅人并进行了史料记载。
当时他本想弄清楚克里雅河最后一滴水流到哪里去了,沿河来到达里雅博依时却发现了一块神奇绿洲,茂密胡杨林里不仅有成群的野骆驼、野猪,更有一个生息在这里的游牧部落。以为碰上了“野人”,他便在考察日记中将他们称为“野人部落”,将绿洲命名为通古孜巴斯特——野猪出没的地方。
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也来到这里,他为克里雅人做了人种学测量,结论是他们是印欧民族的孑遗。是早期成吉思汗远征大军的遗存?是与东进伊斯兰教抗争失败后皈依的古于阗国佛教子民?人们于是这样猜测。
可也有人说,他们是公元九世纪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十七世纪中叶,克什米尔的拉达克进攻古格国,古格城破国亡,其中数十人翻越昆仑败走克里雅河绿洲开荒造田,放牧狩猎,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克里雅人原本就是土著民族,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了。更传奇说法还有很多,比如说他们是两千年前神秘消失的古楼兰人的一支、说他们是西汉时期弥国人的后裔等。
我们也来了。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答案。在翻译艾尼的帮助下我们询问了一位名叫艾买沙迪克的老者。他说,四百多年前,两个牧民为躲避战乱循克里雅河来到了这里。见水草丰茂,胡杨成林,他们定居下来。叫艾买台克登的居克里雅河东岸,叫尤木拉克巴热克的居河西。一河相隔,渐成两大家族,世代联姻,信奉伊斯兰教。如今已繁衍1300多人,老人自己就是艾买台克登氏的后裔。他们一直遵从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住在由红柳和胡杨构架起来的小屋里,以放牧为生。
或许同样遵从的还有远离战乱的祖训?几百年来,他们坚持离群索居,不与外界来往。直到约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不知今夕何夕,谁主天下!当人民政府找到他们时,只见到干涸的河岸边有胡杨树枝围成的、墙上抹了泥巴、屋顶覆有芦苇、屋尖置有一弯新月的清真寺……
一些传承了几百年的风俗
当然,我们此行亲眼所见的克里雅人,早已不再是世外遗民。不过,由于特殊的环境和历史,他们依然保留了很多古老有趣的风俗。
先看其起居习惯,与汉唐时克里雅河发源的众多文明一脉相承——
特殊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牧民居住得非常分散,交通靠马和骆驼。住房则用沙生胡杨木与红柳枝搭建:弯曲的胡杨木并排竖插在地里做支柱,红柳编织成墙体,房顶铺以较厚的芦苇。高出地面约一尺的土沙垒成的台地上,铺上羊毛毡或地毯,就是他们的床了。
每家地上都挖有一个几十公分见方的火坑,这是用来取暖和烧烤美食的。说到胡杨,绝对是他们的密友:他们用胡杨做房屋的柱,把胡杨木从中剖开做门,用胡杨枝生火做饭,甚至死后用胡杨树剖开当棺木……
再说服饰,一样十分独特:男性多黑色长褂、黑色皮帽,习惯性地双手插于袖筒,面带微笑,好奇而有礼;女性则喜穿长袍衫,头披白纱或白纱盖脸,只露鼻梁、眼睛,头戴茶杯口大小的黑色羊皮小花帽。男女平时均赤脚,访友或集会时才穿长筒皮靴。
再说美食。沙漠缺炊具,天生天养的他们发明了自己的美食——“羊肚子烤肉”。那天,我们专门请来附近牧民示范。他们先在营帐旁的沙丘上挖沙生火,3小时后沙子烧得发红,开始宰羊。主刀大叔熟练地剥下羊皮,取出羊胃清理干净,再将羊肉切碎,拌上香料后塞入羊胃扎好,放进烧红的沙坑。又是3小时后,挖沙开胃,倒出了满满三大碗浓汤,一大盘烤羊肉……
再说民风。政府曾力劝他们迁出沙漠,但他们就是不肯——谁会舍得呢?这里民风那么纯朴!村民说,沙漠中如果走访亲戚,一走要几天甚至几周,可走的时候门根本不用锁,门口放把斧子表示家里没人就行了。任何一个路过的外来人,都可推门而入,自己烧火做饭。十多年前,这里成立了乡政府和派出所,但这里唯一的干警至今也没有办过一起案件,后来,这名世界上最清闲的干警开了一个小商店。有趣的是,这商店也从不出售利润较高的香烟和酒——因为克里雅人有句俗话,“抽烟喝酒的人,不要请进家门”。
沙在眼前,家在脚下,严酷已是寻常,守候成为神话。克里雅人顺应自然、泰然独处,烤沙炊饼,哀哭出嫁,保持了非常奇特的生活习俗。
一场每个女人都会哀哭的婚礼
而这“哀哭出嫁”,我们这次竟然有幸亲睹。
克里雅人结婚嫁娶,也会派“喜帖”,不过这“喜帖”很特别——只是一张小纸条,派出之后逐户传递。200多户居民,相距少则几公里、多则二三十公里,因此小纸条至少提前半个月就得发出。
我们到时,正赶上16岁的阿依夏木要出嫁。清晨,铁热木的女人们早早赶到新娘家,那些远在二十公里外的则在头一天就赶到了,一改平时节约用水的习惯,她们几乎清洗了新娘家所有的生活器皿——婚礼在达里雅博依,是当作节日来庆贺的。
午后,迎亲的人来了。新郎带来的乐手在新娘家门外宽敞的沙地上弹琴歌唱,而平常的日子里,这里除了羊的叫声,听不到别的声音。新娘家的女人们一边听着,一边用炙热的沙粒烘烤大饼,用茶水和沙烤饼招待来客。
年轻的乐手们每个人都十分卖力,时歌时舞,引得老人孩子一同欢跳。别忘了这里是沙漠!所以,在那种比手鼓更欢快的节奏里,舞步扬起阵阵尘雾里,只闻歌声不见人,舞者像旋转着的陀螺止不住脚,腾旋起一簇烟柱在空中抖动。
阿依夏木的木屋里,几个女人低声吟唱,歌词里嵌着新娘的人名,几近直白式的对她的安慰。这是一种传统的即兴吟唱形式,一种歌聊,以歌叙事,还不是哭,但已经透出平缓和伤感。
阿依夏木在想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她只在男方提亲时见过新郎一面而已,按照达克里雅人的习俗,缔结婚姻的形式要经过择偶、说媒、赠送彩礼、定亲、婚礼几个阶段,未婚男女单独相处是蔑伦悖理的,他们坚信婚前的纯真才不会导致婚姻兰因絮果的结局。关于夫家,她知道些什么呢?无非是新郎的父亲是70岁的吾甫力?艾山,新郎家有三个男孩,最小的弟弟只有11岁,家里有95只羊,而她将要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下午五时,娘家的女眷们开始为阿依夏木梳妆打扮。阿依夏木已经忍不住了,木屋里不时传来她嘤嘤的抽泣声。七时,迎亲的四个年轻人用一块毛毯将阿依夏木抬出房外,围着木屋转了三圈,完成了出嫁前的告别仪式。当阿依夏木被托举到马背时,送亲的女眷们齐齐掩面抽泣,不是痛哭,但那压抑的唏嘘比撼天动地的痛哭更让人难受。
男人们则显得持重而大度——在克里雅人眼中,婚礼是所有女人的节日,不管男人是否高兴,女人们都可以泪光涟涟地面对他们,因为这也是他们难得看到的女人心灵展示,沙漠中,这种温馨平时是见不到的。
这些长期被当作家庭支柱的女性,在这一天总是异常脆弱,泪水如破堤的河水冲溃情感堤坝,淹没一户又一户人家,丈夫、孩子像是乘坐在无桨的独木舟上,在女人的泪流中飘得心慌,不知何处为家。这无声的泪歌,是达里雅博依女人特有的,男人无法破译。
迎亲的人向克里雅河西岸走去,阿依夏木平时放的羊群尾随到了河边,一只小羊还不小心跌倒在水中。可是,阿依夏木已经顾不上它了:跟往日不一样了,姐姐今天不能带着你们过河了,姐姐东岸的世界已经丢掉了……
等候的人分列河边,井然有序排着队,他们是新郎家的亲友,有的甚至是骑着骆驼从七十多公里的地方赶来的。贺礼整齐地摆放门前,一只被作为贺礼的小羊羔在门口跑来跳去。
伴娘搀着阿依夏木跳过门前火堆时,我在新郎父亲的脸上看到了幸福。新娘和新郎将蘸着盐水的馕饼放进口中咀嚼,意味着他们将厮守一生,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客人也都分得一块,据说,吃了这块馕饼,会给新婚家庭和自己都带来好运气。
阿依夏木自己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礼物,因为在克里雅人眼里,新娘出嫁只是做女人的开始,要到了生养出第一个孩子时才是完整的女人,那时她会得到比出嫁时更多的首饰和衣裙,并从此享有只有在母系社会中才有的尊严。
没有人再哭了。男人,女人,小孩……每一张克里雅面孔上,都漾着笑容。
这一种叫“库麦西”的面制大饼是当地人的主食。制作方法尤为奇特:把沙地烧热后在中间刨一个坑,再将面团做成饼状埋入,几十分钟后取出就可以吃了。面饼与炭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相隔,但饼熟后拍一拍,一点灰土也不会有。人少做小饼,人多做大饼,来客最多时,烤出的饼甚至大如一张圆桌
- · 手工雕刻:针眼里的7匹骆驼[2008-8-18]
- · 奇俗大观:以食品做定情物[2008-8-15]
- · 手指上的奥运会开赛啦[2008-8-14]
- · 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拿的[2008-8-12]
- · 让你匪夷所思的搞怪发明[2008-8-11]
- · “怪物”太岁真能让人长生不老?[2008-8-8]
- · 牛郎织女故事发源地到底在哪儿?[2008-8-7]
- · 牛郎织女鹊桥会 谁家女儿乞巧节[2008-8-6]
- · 游历古都:洛阳铲 奇闻[2008-8-5]
- · 世界各地有趣的公交车站[2008-8-4]

- 酒店
- 特产
- 娱乐
- 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