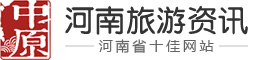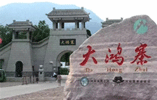将洛阳铲用力插入土中,深深旋转,再拔出,一截带着细密纹路的泥土芯被带出……20年考古勘探生涯,这样的动作崔彦春不知重复了多少回,一把洛阳铲也见证了无数个风吹日晒的日子。
崔彦春是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名考古勘探技术人员,带着熟悉的洛阳铲和多年积累的技术,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他从众多高手中成功突围,获得考古探掘工项目三等奖。

崔彦春在比赛中使用洛阳铲。
“首次到全国舞台进行展示,能获奖感觉很不容易,也看到自己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还需要继续努力。”崔彦春说。
正是对自己的高要求,对考古的深深热爱,让这位老兵坚守考古一线20年,将考古勘探从一份简单的工作,干成了难以割舍的事业。
“刚从市里一个建设工地过来,现在实行考古前置,我们需要提前去进行勘探。”8月15日,在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记者见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崔彦春。
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上的茧子清晰可见,尤其是虎口位置特别明显,这是他常年在一线从事勘探发掘工作留下的印记。
“考古勘探是在发掘前进行勘察,确定遗址、墓葬等的规模、范围,准确确定最佳发掘范围,是考古发掘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崔彦春介绍。
在崔彦春看来,考古探掘工作并不像科研工作那般“高精尖”,自己也只是众多考古技师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努力着。正是许多人“平凡”的努力,才能让后续的考古和科研工作一环接一环地顺利展开。

此次全国比赛中的考古探掘项目,比的就是技术人员勘探和发掘的功力。比赛由理论考核与实操比赛两部分组成。实操比赛中,选手要在层叠堆积的地层中勘探、发掘,尽可能多地完成对遗物的摄影、绘图、记录等工作,采集遗物和多学科研究样本,判断遗物的文化分期和时代内涵。
“比赛现场是真实遗址,考验考古技能的规范性和知识储备,首先想到的还是以最少的探孔数量或对遗址最小的影响,尽可能整体把握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等。”崔彦春回忆。
考古探掘工作首先是个体力活,同时是个心力活。他给记者算了一下,一名棒劳力采用人工方式挖土,一天大约能挖5立方米。比赛中,他在4米长、2米宽的探方中挖了0.6米深,折合挖土4.8立方米,发掘整理了20多件预埋的“文物”。
其实,这些都是20年来崔彦春一直在做的事情。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的考古发掘,到灵井“许昌人”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勘探,再到汉魏许都故城遗址第三次考古勘探,他参与了很多重要项目,布孔、钻探、发掘、绘图、编写勘探报告,一年中近10个月的时间,他和同事们都在中原大地上下求索。

在严冬的野外测量数据,拿着工具的手很快就被冻得没了知觉;在酷暑的考古现场勘探,湿热让人喘不上气;蹲在原地观察地层、辨别文物,有时一蹲就是几个小时……长时间在野外作业,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可他却乐在其中:“能亲手触摸那些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感受它们的存在,再苦也值得。”
干考古,崔彦春其实是半路出家。他曾在部队服役12年,2005年转业到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时已经30多岁。面对全新的领域,他从零开始,在考古一线学习钻研,从“小白”成长为一名行家里手。“当兵的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再苦再难,一定要干好。”崔彦春语气坚定。

参与颍河流域先秦文化调查的崔彦春在一处遗址刮找出的夯土层堆积
虽然已经50岁,但对于新事物他同样玩得转。近些年,他带领的技术队伍不仅加入了很多新鲜血液,更增添了许多高科技硬件和技术,考古勘探如开了“外挂”一般。
崔彦春介绍:“RTK、GPS、全站仪、红外线测距仪、无人机等,这些目前都已经配备,还有3D建模、文物一张图等技术的应用,使古遗迹数据能够真实、准确、全面地保存下来。”
2017年—2018年,为摸清灵井“许昌人”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崔彦春和同事们参与其中,以实地踏勘、人工勘探和机械勘探相结合方式,探明了灵井“许昌人”遗址中心区的堆积深度和核心区域面积,确定文化遗址5处,并通过RTK测绘、无人机航拍等绘制了遗址分布图。
如今,作为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技术骨干,带年轻人成了崔彦春的重要任务。在工作群中,常能看到他为大家解疑答惑;在勘探现场,他更是手把手进行现场教学;在办公室,他也常和年轻人一起交流学习。
他常跟年轻人说:“干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品质是坚毅和果断,在一线要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脑勤。”
干一行,爱一行,择一事,终一生。“未来会踏踏实实、尽职尽责地完成好每一个考古发掘项目、每一次考古工作调查,继续提升磨炼自己的手艺,带出更多新人,为考古事业多出一份力、多做一些事儿。”崔彦春诚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