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别”:再看江郎才尽的背后
http://www.hnta.cn 2008-12-30 来源:大河报 点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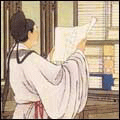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千古一别、千年一叹、千载一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郎一枝五彩生花妙笔,文光射九斗,道尽古往今来庶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的离愁别恨。春水江畔秋山路口,执手相看泪眼迷离,江郎移步换景,用华丽工整的骈体渲染铺陈出凄怨缠绵肝肠寸断的别离场景。与这篇《别赋》一并荣登中国名赋排行榜的还有江郎的《恨赋》。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千古一别、千年一叹、千载一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江郎一枝五彩生花妙笔,文光射九斗,道尽古往今来庶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的离愁别恨。春水江畔秋山路口,执手相看泪眼迷离,江郎移步换景,用华丽工整的骈体渲染铺陈出凄怨缠绵肝肠寸断的别离场景。与这篇《别赋》一并荣登中国名赋排行榜的还有江郎的《恨赋》。 江郎名江淹(公元444年~505年),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南朝著名诗人、文学家,诗赋俱工,辞赋创作以《别赋》、《恨赋》名垂千古。江淹风神俊雅,文华斑斓,自《别赋》、《恨赋》横空出世,墨客骚人无不惺惺惜之唤作江郎,闺阁“粉丝”,朱楼绣阁、庭院深深惦念着冶游或者进京考取功名的冤家,唯有《别赋》可以凭依。一边读一边含泪叹曰:“怎么说到奴家心里了!”小时候老师教习作文,强调好文章的标准乃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写出来能引起共鸣的就是好文章,比如江郎的这篇《别赋》。大家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却迟迟不见江淹有能和《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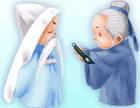 赋》、《恨赋》比肩的珠玑新作问世,朝野上下的“江米粉丝”心绪复杂、相顾长叹:江郎才尽!
赋》、《恨赋》比肩的珠玑新作问世,朝野上下的“江米粉丝”心绪复杂、相顾长叹:江郎才尽! 《南史·江淹传》有段记载,传说江淹当宣城太守时罢官回家,夜宿禅灵寺外阳江的沙洲边,梦见一个自称张景阳的人对他说:“前次我把一匹锦缎寄给你,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从怀中取出数尺锦缎还给张景阳,张大为不满地说:“我给你十丈,怎么用得只剩这点了?”张回头又对旁边的丘迟说:“剩这几尺,没有多大用处,就送给你吧。”丘迟得了张送的锦缎,文思大进,写出了名篇《与陈伯之书》,而江淹却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中也有一段记载,也是说江淹宣城太守任上罢官回家,宿于冶亭,梦见一个自称郭璞的人对他说:“我有一支宝笔放在你那里多年,请即归还。”江淹从怀中摸出五色笔还给郭璞。从此以后,江淹写诗作文再无佳句了。
江郎并非才尽。生逢乱世,这个13岁丧父、曾经采薪养母的苦孩子,随着政权更迭几易其主,从小“公务员”做到“部级干部”,案牍之累使他无暇顾及。最主要的原因是曾经经历的牢狱之灾以及目睹同时代文辞便捷、清丽的才子王融、谢緿因为政治的原因英年早逝,推己及人。还有就是他们单位的“CEO”梁武帝也喜欢写文章,常有“盖世”之作问世,江郎也就噤若寒蝉。
江郎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身世浮沉颠簸之中生命是一座必须保全的青山,哪怕是长久的等待,一定会有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哪怕这个春天是在自己的身后。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懂得取舍,于是神腴骨秀、情远辞丽的江郎交出了“彩锦”和“妙笔”。

作者:宋慧敏
(责任编辑:韶萍) 【回到顶部】 【返回上页】 【关闭窗口】
相关新闻
- 少林弟子释行宇:从苦力强到武痴林 2009-2-16 16:40:50
- 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河南武文斌李隆当选 2009-2-6 8:49:58
- 《少林寺》中牧羊女扮演者丁岚 2009-2-3 15:01:47
- 周杰伦春晚小搭档-河南小子侯高俊杰 2009-2-2 9:18:38
- 河南人李隆:“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 2009-1-19 14:00:11
- “铁军”战士武文斌 2009-1-12 11:40:28
- “北大神童”李书磊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2009-1-9 17:08:30
- 陈建星:壮举感动豫鄂两省 2009-1-6 9:57:11
- 宁饿肚子不受施舍的贤者列子 2008-12-29 14:17:21
- 庞涓:从大梁城到马陵道 2008-12-26 10:34:05






